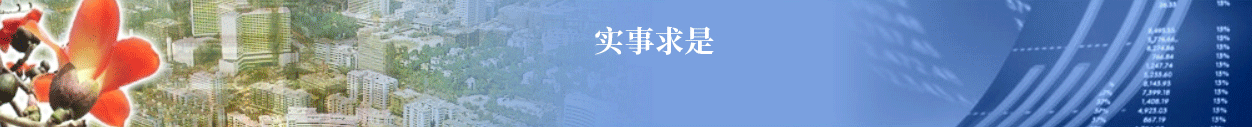十一五成就专栏
“十一五”时期广东收入分配结构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对“十一五”时期广东收入分配结构特征、存在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并提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几点政策建议。
关键词:收入分配 结构分析
“十一五”时期,广东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走出一个“V”型轨迹,期末重新步入平稳较快增长的通道,GDP年均增长12.4%。从“十一五”末期来看,居民收入占比扭转下滑的局面,止跌回升,收入分配呈现结构向好态势,收入调控政策成效初步显现。但在经济较快发展、政府财政收入继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地区、城乡、贫富”三大差距依然比较严峻,收入分配结构还存在着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收入分配结构的基本特征
(一)劳动报酬占比趋向稳定,企业营业盈余提升较快。
“十一五”时期,广东劳动报酬占比延续了以往的下降态势,从2006年的45.4%下降到2010年的44.4%,五年内下降1.0百分点,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下降超过15.0个百分点;而企业营业盈余占比在“十一五”时期则逐年提高,2010年达到27.3%,比2006年上升4.0个百分点,但提升速度略低于“十五”时期,企业营业盈余占比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快速上升的势头出现放缓;生产税净额作为政府在生产领域的所得,其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整体变动不大,“十一五”时期基本上围绕15%波动(见图1)。
(二)在再分配领域,政府、企业和居民呈“一升一降一稳”的特征。
从初次分配结果看,居民在初次分配领域的比重扭转了下降趋势,于2008年达到最低的49.0%,此后两年出现连续上升的势头,2010年达到49.5%。企业所得在初次分配总收入的比重于“十一五”时期基本上相对稳定,2010年占比达到32.9%,比“十五”末期略提升0.3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十一五”初期的水平。政府所得则继续保持上升势头,这一趋势不仅在初次分配领域,在再分配领域同样得到体现。经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所得税等经常转移的调节,最终形成的再分配领域基本表现为“居民稳、企业降、政府升”的局面,整体格局基本稳定。2005年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在再分配领域的比重为48.5:28.6:22.8,到2010年调整为47.5:27.9:24.6,居民占比下降1个百分点,企业占比下降0.7个百分点,政府占比则提升1.8个百分点。特别是2008年以来居民占比相对稳定略有上升。政府占比上升反映出政府在经常转移过程中,其收入来源的所得税规模不断扩大,但政府对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支出规模未能同步推进,从而导致政府占比出现提升。
(三)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趋于加快,农民收入增速近期显著提升,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出现缩小。
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三大经济主体分配格局不断调整之际,居民内部,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对比也出现新的变化。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015.58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079.78元,两者相差10935.80元,前者为后者的3.2倍。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897.8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890.25元,相差16007.55元,前者为后者的3.0倍。虽然绝对差距在扩大,但相对差距缩小了0.2倍。
从增长速度来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十一五”末期改变了以往增速相对缓慢的态势,加快增长的势头明显,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明显快过城镇居民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分别达到了7.6%和8.3%,前者低于后者0.7个百分点,而在“十五”期间前者快于后者3.9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趋于加快,且在“十一五”末期表现更为明显。和GDP增速对比来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分别低于同期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8个百分点和4.1个百分点,但在经济放缓,居民收入增速加快的双重影响下,增幅差距在不断收窄,经济发展开始更多惠及民众(见图2)。
(四)城镇居民内部贫富差距也从高位逐步回落,农村居民收入趋向相对稳定。
城镇居民方面,根据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从2006年的0.3493下降到2010年的0.3356,比起“十五”初期基尼系数接近警戒线0.4的水平已有较大改善。农村居民方面,根据人均纯收入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在2010年达到0.3021,整体来看,“十一五”时期相对稳定,变化不大(见表1)。
表1 “十一五”时期城乡居民内部基尼系数计算结果
|
年份 |
城镇居民(七分法) |
农村居民(五分法) | ||
|
总收入 |
可支配收入 |
总收入 |
纯收入 | |
|
2006 |
0.3552 |
0.3493 |
0.3052 |
0.3082 |
|
2007 |
0.3448 |
0.3447 |
0.3169 |
0.3105 |
|
2008 |
0.3517 |
0.3488 |
0.2961 |
0.3027 |
|
2009 |
0.3416 |
0.3412 |
0.3108 |
0.3060 |
|
2010 |
0.3339 |
0.3356 |
0.2958 |
0.3021 |
注:城镇居民基尼系数按最低收入、低收入、中等偏下、中等收入、中等偏上、高收入、最高收入户七分级计算,农村居民基尼系数按最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中高收入、高收入户五分级计算。
(五)相对差距显著缩小,地区差异系数已出现收敛。
目前,珠三角地区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而粤东、粤西和粤北山区则整体发展相对滞后,这种地区发展的绝对差异于“十一五”时期仍在强化,但地区发展差异系数已于2005年达到近期高位,最近几年不断回落。
2006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为深圳市,达到68441元,最低梅州为8474元,相差59967元。2010年,两者绝对差距进一步扩大到79742元,但相对差距从8.1倍缩小到6.5倍。依据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计算的地区加权差异系数看,整体出现“倒U”走势,从2005年高位回落,到“十一五”时期逐年降低,2010年为0.6333,这一数据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最低水平,非珠三角地区增速加快从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逐步显现。
二、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劳动报酬占比仍在下降,居民所得处于较低水平。
“十一五”时期,企业营业盈余占比不断攀升,而劳动报酬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从45.4%下降到44.4%。相对于政府和企业来说,居民在初次分配总收入和再分配总收入的比重相对偏低,2008年广东居民所得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占比分别为49.0%和47.4%。同年全国两项占比分别为57.2%和57.1%,广东低于全国水平接近10个百分点;相比广东仍处于较低水平,提高居民收入任重道远。
(二)居民收入增速慢于经济增长,普惠发展成果有待努力。
“十一五”初期的2006、2007年,经济增长高位运行,但城乡居民收入则相对较慢,与GDP增速有较大差距。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省经济放缓,同时收入分配政策出现调整,强调公平和效率同等,不断加大对居民收入的政策倾斜力度,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显著加快,与GDP增长的差距逐渐缩小,2009年还超过GDP增长,但2010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出现回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又重新回到低于GDP增速的路径上来。从整个“十一五”时期来看,城镇、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低于GDP增速超过4个百分点。
(三)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不断拉大,贫富差距问题不容忽视。
从城乡居民收入对比看,虽然相对差距在缩小,但绝对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居民内部贫富差距与 “十五”时期相比出现缩小,但基尼系数仍接近0.4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如果考虑到抽样方法和基础数据存在的误差,贫富差距实际上可能要更为严重一些。根据有关学者研究表明,高收入人群样本代表性存在问题,部分灰色收入无法准确反映,低估了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
(四)财产性收入偏低,经常转移规模较小,再分配环节调整力度不足。
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财产收入为956.60元,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达4.0%,比2006年提高0.5个百分点,提升幅度相对缓慢。在全部可支配收入中,利息、股息与红利收入合计占比远低于出租房屋收入占比,投资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农村居民纯收入中的财产收入占比变化不大,甚至2010年还低于2009年的水平。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财产收入占比应该有一个较大提升,但受制于现有融资市场的缺陷,财产收入还相对较低,这也成为导致居民所得在初次分配总收入占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从资金流量的核算结果看,与初次分配相比,居民所得占比在再分配领域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反映了经常转移过程中,对居民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提高偏慢,再分配环节调节力度相对不足。
(五)分行业工资差异显著,部分垄断行业高工资特征明显。
从分行业工资水平看,由于知识性特征不同、体制因素(如垄断)等原因,工资分布的行业差异依然较大。2010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最高为96974元,分布于金融行业;最低为农业部门的15302元,两者相差81672元,前者为后者的6.3倍。和“十一五”初期相比,平均工资绝对差距扩大37349元,相对差距扩大1.3倍。在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在不同行业之间差距在扩大之外,不同行业工资水平的差异系数()也从2006年的0.3802上升到2010年的0.4051。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信息传输业等行业,由于行业垄断,其工资水平在全行业中处于较高水平,这一特征在“十一五”时期没有根本改变。
三、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不利影响
(一)消费所占比重偏低。
近年,国民可支配收入中,居民所得占比持续走低,给三大需求结构带来了负面影响,直接造成居民消费占比偏低。消费与收入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前者由后者所决定。居民所占比重下降,降低了居民消费需求。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使得农村居民消费意愿高而支付能力低,而城镇居民由于社会保障水平滞后,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增大,导致城镇居民消费意愿低而储蓄意愿高,进一步降低了最终消费比例。而企业和政府所得不断提高,企业出于利润考虑,政府源于政绩需要,双重因素带来投资冲动,推高了投资率的持续上升。从而造成投资驱动、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不断强化。
(二)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收入差距加大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存在陷经济于停滞以致后退的风险。当前,改革已走过初期的增量改革阶段,进入深水区,向前推进就要调整现有利益格局,阻力会比较大。2010年,广东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608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地区水平,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期,迫切要求原有以效率优先的分配方式需做调整,提高公平分配的地位,以此为起点,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伐,谨慎推进社会改革,否则,经济结构失衡,经济无法实现转型升级,将重蹈“拉美化”的旧路。
(三)将会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的安全稳定。
改革初期,以效率优先的分配政策利于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打破平均主义的桎梏,促进生产发展。但是,如果一味强调效率优先,贫富差距扩大到社会无法承受的极限,将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给社会稳定带来挑战。已有研究表明,贫富差距扩大将在社会心理、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方面带来了极大负面影响。当前,虽然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相对较高,但由于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升,社会保持相对稳定,也即是社会学上说到的“上升流动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如果一旦“上升流动”停滞,而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将会面临着灾难性的后果。当前,各种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呈现,其反映的主要还是不同群体的经济利益诉求,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对保持社会稳定、成功构建和谐社会将起到积极作用。
四、合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几点建议
(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提高劳动报酬占比。
“十一五”后期,受多种因素影响,整体经济进入平稳增长阶段。在当前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局面下,应当把“做大蛋糕”和“切分蛋糕”,以及提高质量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保证经济增速维持在一定水平和质量之上,在此基础上,通过政府政策指导,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不断改善企业用工环境,扭转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强势地位,从而提高劳动报酬在地区生产总值的占比。
(二)拓宽投资渠道,扩大居民财产收入来源。
财产性收入增长相对偏慢成为影响居民在初次分配中占比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拓宽投资渠道,规范融资市场行为,合理引导居民扩大对直接融资市场的投资,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创新工作,丰富金融投资工具。同时,提高居民投资意识,正确树立效益和风险观念,分流对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资金,全面提高财产收入占比。
(三)增强社会保障能力,提高经常转移规模。
在当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投入规模,特别是城乡居民养老、医疗等领域应重点关注,从而,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强消费能力,也有助于改变过高储蓄率带来的负面影响。发挥政府在经常转移中的主导作用,积极推动扶贫工作走向深入,提高经常转移的规模,实现对收入再分配的有效调节。
(四)以法律制度保障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实现。
解决形成贫富差距的深层次机制和原因,改变只强调效率优先的分配政策,更加注重公平在分配领域特别是再分配领域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效率属于经济学,而公平则在社会学领域,当前贫富差距扩大与市场化推进有着直接关系,这就需要政府宏观调控进行纠正,把公平和效率放在同等地位,从法律制度的形式有效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比重,调节过高收入,打击非法收入,最终形成一个“橄榄球”型的居民收入格局。
(五)加大“双转移”推进力度,区域、城乡协调发展。
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是实现转型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收入格局优化的重要体现。当前,珠三角与非珠三角地区、城乡之间的绝对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协调发展之路面临着严峻挑战。加大“双转移”的推进力度,加快产业转移园的起步、发展、壮大的步伐。在珠三角地区经济逐步放缓的背景下,重点加大对非珠三角地区的投资力度,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以成功实现加快发展、跨越发展的目标。
供稿单位:国民经济核算处
撰 稿:杨少浪 李华 贝燕威
W020110919597267652000.GIFW020110919597267651397.GIFW020110919597270003119.GIFW020110919597272184925.GIF